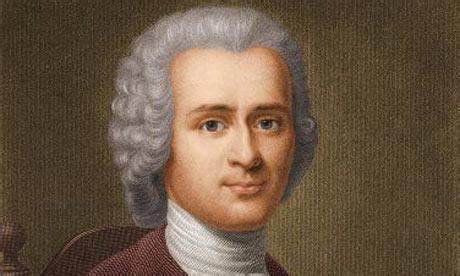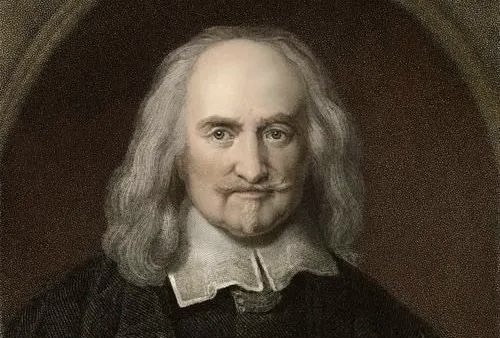启蒙主义者
贝尔的怀疑论
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 1647—1706年)
法国哲学具有怀疑论的传统,早在16世纪,蒙田运用怀疑论鼓吹宗教宽容,笛卡儿也用怀疑论说明传统知识的不可靠。贝尔的怀疑论也有同样的目的。他认为怀疑论的精神实质是理性批判、探索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所有哲学家全都是学园派和皮罗派”。怀疑论的目标不是针对科学和社会的,而是针对宗教神学的。他指出一切神学问题和争论都是混乱、无意义的。像恩典和意志自由、恶的起源和上帝的全能、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等教条教义都没有理性的确定性,通不过怀疑论的考察。
贝尔指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我们不能用信仰来否认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理性不能否认信仰。他的怀疑论的结论是:既然我们既不能证明信仰为真,也不能否定信仰为假,那么,我们对于宗教信仰就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从宗教宽容的目的出发,贝尔怀疑论的最后归宿是信仰与理性的“双重真理论”。这与后来的百科全书派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宗教和基督教信仰进行的激烈批判是截然有别的。贝尔批判的只是神学以及一切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的哲学理论,但他并没有批判信仰本身。相反,他说,信仰来自“启示之光”,理性是“自然之光”,信仰在理性之外,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确定性和真理性。宗教信徒完全有相信天启和神迹的正当权利,只要他们不把自己的信仰混同为理性,他们的信仰就是无可怀疑的真理。
贝尔不但把理性与信仰分开,他还用同样的方式把道德与宗教分开。他说,道德的基础不完全是信仰,理性对实际环境和行动后果的算计也可使人趋善避恶。
他建议把“对上帝的畏惧和爱慕并非永远是人们行动的最积极的原动力”列入一般的道德准则。按照这一道德准则,异教徒和无神论者都可行善,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秩序良好、道德高尚的社会,无神论者尤其是这样。他以遥远的中国为例,说明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当时德国的弗雷德利克大帝在评价启蒙学者的贡献时说,贝尔开始了启蒙的战斗,一批英国哲学家跟随其后,伏尔泰最后决定性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年)原名查里·德·色贡达(Charles de Secondat),孟德斯鸠是他的男爵称号。
孟德斯鸠是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各个民族的法律都进行了概括。他把造成种种法律的不同原因归纳为民族性格、政体形式、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总和就是他所称的法的精神。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不仅是经验事实的概括,更重要的是理性的原则。
他所建构的原则就是当时流行的自然法的观念,他的法哲学的特色是说明了自然法的理性基础及其在社会政治中的运用。从广义上理解,自然法是“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说:“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实体都有它们的法,神有神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人之上的天使有天使的法,人有人的法。”一切实体都遵循法,即使神也不能例外,造物主对世界的统治依法进行。“因为世界没有这些法则是不会存在的。这些法则是一种确定不移的关系。……每一种特殊都有齐一性,每一种变化都有恒定性。”不难看出,神的法则相当于自然规律。孟德斯鸠用自然法否认了神迹和启示,使法成为理性可以认识的对象。
孟德斯鸠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人法。他说:“理智界远不如自然界治理得那样好。”人作为自然实体,受不变的法则支配;但人同时也是理智实体,他的有限知识和脆弱的感情阻碍或改变着法则。因此,人不能成为自己制定的成文法的基础。自然法是客观的“公正关系”,先于成文法的基础。孟德斯鸠承认,在人类进入社会状态之前,有一个被自然法所支配的自然状态,但他没有论述人是如何以及为何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他的主要任务是从自然法中寻找他所看到的种种成文法的合理的基础。
孟德斯鸠说,自然法与人的本性和生活条件相吻合,是“惟一从我们的存在结构派生出来的”。自然法的应用范围包括和平、自养、互爱和社会生活。战争起源于社会,包括国与国、个人与个人的战争,“战争状态乃是促使人间立法的原因”。为了战争与和平的目的而制定的成文法包括国防法、政治法和公民法,等等。成文法要符合建立政府的“本性和原则”,尤其要适应一国的自然状况,因为地理环境决定着民族性格和社会制度。孟德斯鸠着重讨论了气候、土地、海洋对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影响,但这不能表明他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全面地看,孟德斯鸠的观点是,自然法是决定成文法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依据,但不同的民族根据自然法决定他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时,受到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不同的条件下,自然法派生出三种政体: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共和制是全体或一部分国民的统治,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民主制,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贵族制。君主制是一个人按照基本的法则,并通过中介的力量进行的统治。专制是独裁者的既不依照法律、又不通过中介力量的任意统治。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社会风俗,共和制的社会遵从公德,君主制社会崇尚荣誉,专制社会充满恐惧。
孟德斯鸠批判法国的专制制度,并不是因为它违反了自然法,而是因为它不符合法国的国情。他拿法国和英国进行对比,认为两国的民族性和地理环境差别不大,但政治和法律差别却十分显著,可见是一些人为的因素阻碍了法国人合理地运用自然法。他主张法国向英国学习,采用民主制度。他对三权分立的合理性的论证比洛克更加深入,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设计了政治蓝图。
伏尔泰的理神论
伏尔泰(Voltaìre, 1694—1778年)原名为弗朗索瓦·阿鲁埃(Franscis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平民家庭,毕业于耶稣会办的大路易学校。
伏尔泰对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进行了激进的批判,批判的对象不仅仅是信仰的非理性,而且是迷信的非人性的罪恶。他甚至用“两足禽兽”、“败类”等激烈语言攻击僧侣阶层。但是,伏尔泰不是无神论者,相反,他不满意笛卡儿的哲学经过斯宾诺莎而导致无神论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理神论”(deism,也译为自然神论)与“有神论”(theism)有别。有神论的反面是无神论(atheism),理神论和泛神论(pan-theism)介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一般说来,泛神论否认超越或独立于世界的神,理神论否认人类理性不可理解的神,两者都可能导致否认有人格的神的无神论;但是,泛神论和理神论毕竟承认神的存在和智慧、全能等属性,往往和有神论一起反对无神论。
伏尔泰从牛顿物理学中找到上帝存在的充分理由。他说:“牛顿的全部哲学必然导致关于一个最高存在者创造一切、安排一切的知识。”在《形而上学论》中,他把宇宙看做一座钟,引力是发条,各部分可以精确地、和谐地运转,需要外力推动,必须有一个最初的推动者。同时,物质的存在也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因为自然界有真空,所以物质是有限的;如果物质是有限的,它就是偶然的,依赖外力的;因此,运动和引力不是物质的本质,而是被上帝置入其中的。按照同样的推理,伏尔泰说,没有证据表明上帝不把思维也置入物质之中。这句话并不能说明伏尔泰相信物质能够思维的唯物主义观点,相反,他相信物质本身既不能运动,也不能思维;如果物质确实在运动和思维,那只能是上帝的工作。
但是,上帝只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和自然规律的制定者,他在创世之后,便不再干预,他犹如一位建筑师,在完成宇宙大厦之后,不再过问大厦的使用;从严格的决定论出发,他还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他说:“任何事物都有原因,人的意志也有原因,人的自由都是他最终接受的观念造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的理神论带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
上帝的存在不仅对于理性是必然的,对道德世界也是必要的。社会没有正义不可能维持,没有上帝的赏善罚恶,正义就不能在人心中维持。一般民众不是哲学家,不能靠理性来决定自己的道德准则,需要宗教信仰作为道德的前提。但他反对利用上帝观念,制造迷信、狂热和专制。他的理神论信仰和宗教宽容思想也是一致的。他推崇英国的宗教宽容,指出那里有三十多种宗教,人民却能和平地幸福生活。英国的开明君主(君主立宪)制使得君主有无限的权力行善,却无力为非作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