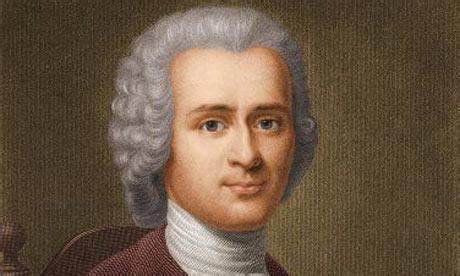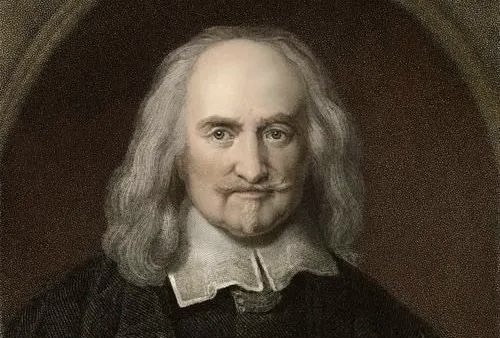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Plotinus, 204—270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太一、理智和灵魂为“三个首要本体”。“本体”(Hypostasis /Principle)一词被普罗提诺赋予独特的意义,与过去出现的“是者”、“实体”、“基体”等范畴相区别。普罗提诺所谓本体指最高的、能动的原因,现代人也把它译为“原则”。严格地说,本体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神。
第一本体“太一”
“太一”(to en /the One)指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太一”这一中译概念取自《庄子·天下》中概括老子学说的一句话:“主之以太一。”如同老子的“道”既是有、又是无一样,太一有肯定和否定两重规定性。肯定地说,太一是善本身。它的善不是伦理之善,而是本体的完善和圆满,或者说,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否定地说,太一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万物的总和,而是先于万物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与任何一个有生命、有力量的东西相等同。太一无形式、无德性、无意志、无思想、无意识、无运动、无变化。因为太一不具备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单纯的统一性。一切能肯定的东西都有它的对立面,都是区分和分割的结果,只能归属于“多”,而不是“一”。太一也不是理智的对象,因为理智只能靠概念和范畴去把握对象,而一切概念和范畴都需要区分才能被定义,因此只适用于能被分割的东西,但不适用于不可分割的太一。总之,太一是不可名状的,不可认识的。
普罗提诺特别强调太一的否定特征,以此说明它超越了“是者”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质,太一不是一个东西,而是“是者”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东西之所以为是者,首先因为它有某种统一性。在此意义上,他说:正依靠太一,是者才是一个东西。除去太一,是者就不再是什么东西了。……任何东西失去了其所是。这段话表明,普罗提诺意识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原则的分歧,他同意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原则,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是者”作为最高原则。
流溢说
普罗提诺虽然没有用过多的概念来规定太一,但却用形象来比喻它。太一时常被喻为“太阳”、“源泉”。按照这些比喻,太一虽然不运动,但却能生成其他本体,这一生成过程被喻为“流溢”。这一比喻有两方面意义:其一,太一的生成并不是主动的创造,创造是一种外求的活动,但太一却是完满自足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更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生成其他本体”。或者毋宁说,流溢是善的自然流露。其二,流溢是无损于自身的生成,正如太阳放射出光芒无损于自身的光辉一样。太一的生成是完善的本性所在,是自满自足、产生外物而又无损于自身。
第二本体“理智”
理智或心灵是最先从太一中流溢出来的本体,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原初的绝对统一性,它包含着一些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肯定性质,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示它。当然,理智仍然享有太一的统一性,因此,被区分出来的多样性仍然是统一的。如果说太一是绝对的一,理智则是一和多的统一。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理智本体是理念型相的领域。
普罗提诺还进一步说明了适用于理智的范畴,它们是:思想和存在、异和同、动和静。以上六范畴基本取自柏拉图的“通种论”。普罗提诺认为,通种只适用于第二本体“理智”,因为它们是区分的产物,不能适用于不能被区分的太一。通种表示的三组区分是最高的理智区分,是区分一切可感物的前提。
第三本体“灵魂”
灵魂从理智中流溢出来。普罗提诺说,理智的流溢是对太一的流溢的模仿。作为第三本体的灵魂即柏拉图所说的世界灵魂,它是一种能动力量。它的能动性表现在变动不居,活跃于各个领域,既可以作用于和自己本性相一致的理智和太一,也可以作用于和自己本性不一致的低级对象。或者说,灵魂既是一,又是多:当它与理智和太一相通时,它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当它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之中时,作为推动事物变化的内部动力,它是多。
普罗提诺使用哲学与宗教相混杂的表达方式说,太一、理智和灵魂是三个本体,但又是同一个最高的神。他和其他希腊人一样,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但他在哲学上却是一神论者。用单数大写的神表示三大本体。用哲学的语言说,神即是一,或是绝对、纯粹的一(太一),或是一和多的统一(理智),或既是多,又是一(灵魂)。就是说,三个本体为同一位神。后来的基督教教父将“本体”译为神的“位格”,把神作为单一实体,引申出上帝“三位一体”的概念。
可感世界
普罗提诺承认在三大本体之外,还有质料。质料没有任何规定性,包括形状的规定性,但质料不是“虚无”,而是“非是者”、非存在。非存在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团漆黑的混沌。排除了事物所有性质之后,事物不成其为事物,剩下的只有质料。正如涂抹一切颜色之后仍有黑色一样,质料并不是完全虚无的状态。
质料和太一是对立的两端,犹如黑暗与光明的对立。正因为如此,由太一发端的流溢终止于质料,犹如光线不能穿越无际的黑暗。然而,灵魂以其活跃的能力,却能与质料相结合,产生出个别的、可感的事物,它们的总和就是可感世界。
人的灵魂
人生活在充满灵魂的可感世界,人的灵魂与周围的灵魂相通,普罗提诺称之为“同情”。这种作用力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一种物理(自然)的力量,推动着人的活动。但是,人的灵魂不是完全被决定的。普罗提诺承认人有自主的能力,因为影响人的灵魂的“灵魂”本体处于中间地位:一方面可以上升到最高本体,另一方面可以下降到可感世界。同样,人的灵魂既可以通过思辨和观照追求神,也可以耽于肉欲而陷入身体不能自拔。应该注意的是,人的灵魂两种相反的能力并不表示自由状态,恰恰相反,它表明灵魂无自我完善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受外部力量的影响。
普罗提诺没有“自由选择”的观念。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意志的自由选择表现在人们对“应当做什么”的思虑的结果;按普罗提诺的说法,人不会自觉地思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因为“自觉”和“专注”成反比关系,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时,他不会自觉地思考这件事的性质,正如一个专心读书的人,不会对读书这件事有自觉意识。对他来说,人的灵魂决定做或不做什么时,都不自觉地受到外部灵魂的影响。
灵魂的上升
人的灵魂被禁锢在肉体之中,人的灵魂朝向本体或神的上升活动是摆脱肉体的唯一途径,具有趋善避恶的伦理价值。
灵魂如何回归到神呢?普罗提诺要求通过德性的修养,净化灵魂,经过对神的沉思,最后达到观照神的最高境界。观照使人达到迷狂境界。迷狂是比幸福更强烈、更充实的生命体验,是灵魂出窍、舍弃躯体与至善的太一合一的不可名状、无与伦比的神秘状态。神人合一的思想是普罗提诺给柏拉图主义注入的新内容。
希腊哲学的衰落
公元529年关闭雅典的哲学学校只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希腊哲学业已衰落颓败。希腊哲学的衰败不但有表可征,而且有因可循。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端对希腊哲学的性质做了精彩总结。他认为哲学起源于诧异,哲学家追求非实用的智慧,哲学是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事业。正是这种特有的纯思辨精神,使得希腊人创造出周围民族所没有的文化形态——哲学。尽管希腊哲学也包含非理性因素,具有现实针对性,但它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的沉思和超脱的静观。它的优越性同时孕育着危险。理性思辨或囿于自身领域而维持自足和纯粹,或满足外在需要而与宗教、道德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在前一种情况下,纯理性思辨自身不能克服内部争论和冲突,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在后一种情况下,伦理化的哲学一旦不能满足民众的道德追求,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我们在罗马后期看到的就是希腊哲学各派这样两种结局。学园派和怀疑派的思辨和争辩否定一切普遍的、公正的规范和标准,破坏了一切理论基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树,这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思潮从内部阻止希腊哲学发展,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探索蜕变成为否定而争论的理性自杀。伦理化的哲学也逐渐丧失指导道德实践的功能。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被歪曲为纵欲主义,唯物主义被庸俗化为物质利益至上,成为贵族和富人放纵无度的享乐生活的辩解和安慰。斯多亚派堕落为一种“官方哲学”,他们宣扬的节制、忍让、服从命运、安分守己、尽忠尽责、热爱他人的说教,与罗马统治者残暴、奢侈和争权夺利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斯多亚派学说丧失了道德哲学所必需的实践性和说服力,成为贵族们寄托精神的清谈和空想。至于后起的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修行方式流为迷信和巫术,和各种荒诞的偶像崇拜相掺杂,也不能为哲学理论发展提供动力。事实表明,希腊哲学已丧失了自身的活力,不能作为积极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必须被吸收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之中才能保存自身价值。历史证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新兴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兴起是希腊哲学衰亡的外部原因之一。基督教以其素朴的信仰取代繁芜的思辨和论辩,用新的伦理化宗教的理想满足了人们的道德追求,因而在与希腊哲学优胜劣汰的斗争中战而胜之,取而代之。